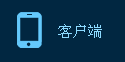出家,各有各的因緣
“寺里‘明’字派的法師,后面那個字都有講究。明海師,海納百川;明影,外界的一切都是內心的投影;輪到我,辛苦死了,要學玄奘啊。”明奘法師喜眉笑眼。
“來來來,她們是我的粉絲團。”他招呼著房里的幾位年輕女尼,她們身后又站著幾個大學生。“她們都是大學生出家。我還上網瞧過那個柳智宇,專門打電話到龍泉寺問過,他還在寺里面。他不是僧相,也沒僧氣,他太有棱角。你看看星云大師,他也受全球矚目,但是他身上有僧氣。僧人哪怕再有個性,棱角也要深藏其中。”明奘法師指指《南方人物周刊》的專欄。
“我們害苦了柳智宇。他出不出家原屬個人行為。出了,后來發現不行了,還能回到過去的圈子里。現在完了,三十六計中‘上樓抽梯’——上了個半截子,梯子抽走了。他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來。別擴大他,好么?這個社會需要精英分子出家,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這時,他才正色道。
據傳,他離開柏林禪寺,在北京懷柔的朝陽寺任方丈,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課。在漢傳佛教講經大會上,別人的嚴謹分析打耳邊穿過,他則用他的“電子小玩意”偷看當紅的網絡小說《陽神》。
有人在網上批他“有拂佛理”,但佛門清規戒律似乎約束不了他,但他的弟子們說他用大白話講解《金剛經》明快了然,招人喜歡。
問他為什么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較怪,就是想過一種比較古老的日子——
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績在全班63個學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結果我沒讀幾天,便寫了退學申請。現在如果把它搜出來,就是一篇反對中國教育體制的檄文。
遞交退學申請時,我找系主任談,找學生處談,他們全來勸我。逼得我直接跟黨委書記說,咱倆不如換個位置。我要是您,勸人都會比您說得有水平。
這句話把他氣得夠嗆,他是從越南前線回來的老軍人。如今想想,我那會兒就是一個狂妄的憤青。可我就是在那個教育體系里面,找不到我想要的東西,我不想浪費我的生命。
當年的教育體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歷史課本里,老子、佛陀從沒出現過。等上大學,參加完軍訓后,我讀到了一本《壇經》。讀完以后,我就說我是個和尚。
退學后,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做內刊當編輯。精神上、言論上自由許多。單位里全是一群哥們,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將。
好多人勸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時候,我一人老往廟里跑,坐在那里面安安靜靜體驗。這是屬于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禪寺我也這樣。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禪學社幾個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禪寺。禪寺在建觀音殿,我幫著干活。
在那里,我第一次瞧見了老和尚(凈慧法師),遠遠觀察他走路的樣子。我直覺告訴我,他就是我的師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說,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說好。這就行了。
我懷揣一千元、十本書、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禪寺,走前根本沒料到會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里的書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別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寺院里也是這樣。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學夏令營活動,派我專門照顧那些講課的禪師。我給他們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彌、僧人逮個機會就在齋堂里向他們請教。我整天守著他們,從來不問問題。當時佛教協會的妙法法師很奇怪,問我你怎么沒有問題。我說我真沒有問題。他說,那你來干嘛?我說,我來出家。
他說,你肯定能做個和尚,因為你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