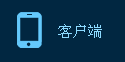我在家里住了十八年,但進入阿里和哈桑房間的次數寥寥無幾。每當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開了。我穿過那片薔薇,回到爸爸的廣廈去;哈桑則回到他的寒廬,他在那兒出世,在那兒度過一生。我記得它狹小而干凈,點著兩盞煤油燈,光線昏暗。屋里兩端各擺著一床褥子,一張破舊的赫拉特(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出產的地毯四邊磨損,擺在中間。屋角還有一把三腳凳,一張木頭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畫畫。此外四壁蕭然,僅有一幅掛毯,用珠子綴著"Allah u akbar"(真主偉大)的字樣。那是爸爸某次去麥什德(Mashad,伊朗城市)旅行時給阿里買的。
1964年某個寒冷的冬日,正是在這間小屋,哈桑的母親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媽媽因為生產時失血過多而謝世,哈桑則在降臨人世尚未滿七日就失去了母親。而這種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數阿富汗人看來,簡直比死了老娘還要糟糕:她跟著一群江湖藝人跑了。
哈桑從未提及他的母親,仿佛她從未存在過。我總是尋思他會不會在夢里見到她,會不會夢見她長什么樣子,去了哪里。我還尋思他會不會渴望見到她。他會為她心痛嗎,好比我為自己素昧平生的媽媽難過一樣?有一天,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電影,我們從爸爸家里朝扎拉博電影院走去。我們抄了近路,穿過獨立中學旁邊的軍營區——爸爸向來不許我們走那條捷徑,但當時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們跨過圍繞著軍營的藩籬,跳過一條小溪,闖進那片開闊的泥地,那兒停放著積滿塵灰的廢舊坦克。數個士兵聚集在一輛坦克的影子下抽煙玩牌。有個士兵發現了我們,用手肘碰碰身邊的家伙,沖哈桑嚷嚷。
“喂,你!”他說,“我認識你。”
我們跟他素不相識。他又矮又胖,頭發剃得很短,臉上還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臉帶淫褻,朝我們咧嘴而笑,我心下慌亂。“繼續走!”我低聲對哈桑說。
“你!那個哈扎拉小子!看著我,我跟你說話吶!”那士兵咆哮著。他把香煙遞給身邊那個家伙,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圍成圓圈,另外一只手的中指戳進那個圈圈,不斷戳進戳出。“我認識你媽媽,你知道嗎?我和她交情不淺呢。我在那邊的小溪從后面干過她。”
眾士兵轟然大笑,有個還發出一聲尖叫。我告訴哈桑繼續走,繼續走。
“她的蜜穴又小又緊!”那士兵邊說邊跟其他人握手,哈哈大笑。稍后,電影開始了,我在黑暗中聽到坐在身邊的哈桑低聲啜泣,看到眼淚從他臉頰掉下來。我從座位上探過身去,用手臂環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臉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認錯人了,”我低語,“他認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