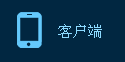像“恐怖分子”一樣被押送回國
記者:律師稱你是像“恐怖分子”一樣被押送回國的。是這樣嗎?
翟田田:按照法律程序,自動離境應該是由我自己離境,但有一個人可以跟著我辦手續,但實際上我是被囚車送到機場,腳上戴著鐐銬,腰上纏著鐵鏈子,手銬和鐵鏈子連著。看守人員在囚車上給我一個三明治,我要彎下腰才能吃到。在機場我沒能見到律師、朋友和華文媒體,也沒能拿到我的行李。對方給出的理由是擔心送我的人把我打倒,這個理由非常可笑。我隨身帶的只有一個在監獄里藏的塑料袋。當時身上的錢還剩40美元,我花27美元買了一個最便宜的小包。從進入機場到臨上飛機,所有人都看到我戴著手銬腳鐐的樣子,我不愿意再回憶這段屈辱的經歷。
翟泰山:田田昨晚睡覺脫下襪子,我看到他的腳脖子被腳鐐勒出了傷痕,非常難過。
校方找不到起訴理由
記者:檢方為什么直到現在都沒有起訴你?
翟田田:校方知道沒有起訴我的理由,只想隨便找個罪名吊銷我的簽證,遣返我回國。他們以為我在魚龍混雜的監獄里呆不了多久就會堅持不住自動認罪,這樣他們做的所有事情就都變成合理的了。沒想到我硬是堅持了幾個月。檢方本應在6月1日起訴我,但因為沒有證據一直拖到現在。
記者:白人女子羅紅玫曾控告你“騷擾”,這是你被校方開除的理由之一嗎?
翟田田:我和羅紅玫是經我的博士生導師介紹認識的。這是我的個人生活問題,與此案沒有任何關系。因為我的律師海明要求校方提供停學理由,他們才搬出了這個案件。
記者:媒體和公眾在這個案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翟田田:如果沒有媒體的報道和公眾的關注,也許我今天仍然在坐牢。中國媒體關注了,美國的華文媒體關注了,我的罪行才得以一步步減輕。直到我絕食抗議引起《紐約時報》關注,直接打電話給檢控官,我才得以從刑事監獄被轉移到條件好一些的移民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