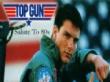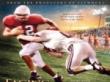最不像斯科塞斯的影片
這個經典的愛情故事沒有馬丁·斯科塞斯以前影片一貫所有的流血和大喊大叫的“Fuck you”,這個總是憤怒的導演這次呈現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性欲和讓人愉悅的羅曼司。
影片背景設置在19世紀70年代,那時的人們按照嚴格的社會禮儀談話、走路、見面、聚會、進餐,甚至他們個人的生活、戀愛和婚姻也在這種程式下進行,雖然這種社交禮儀的密碼并沒有任何書面記錄,但生活在其中的人自出生以來就在不斷地對它進行著研習。小說作者伊迪絲·沃頓以強烈的諷刺口吻將那一時代稱為“純真年代”,這一看似已成為過去了的年代在現今的社會依然以喬裝改扮過的面容繼續存在。雖然影片展現的是19世紀70年代紐約上流社會的愛情悲劇,但斯科塞斯以往影片中顯見的流血和沖突卻被隱藏在看似優雅和文質彬彬的社會禮儀之下,這種表面的文雅端莊之下卻是精于算計的殘忍。雖然相隔了一個世紀,但馬丁·斯科塞斯和伊迪絲·沃頓都是研究紐約部落戰爭的專家。
這類題材的故事在此以前已被反復拍過,如《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波士頓人》(The Bostonians)即是此類題材的上作,這類題材表面上看似和拍出了《窮街陋巷》(Mean Streets)、《出租汽車司機》(Taxi Driver)、《憤怒的公牛》(Raging Bull)、《好家伙》(Goodfellas)等片的馬丁·斯科塞斯毫不相干,這類題材似乎是對所謂“純真”的一種挑釁和譴責,但當他的朋友和合作編劇Jay Cocks(前《時代周刊》的電影評論家)將伊迪絲·沃頓的小說《純真年代》拿給他看時,馬丁·斯科塞斯立即對這本小說著了迷,他在后來的一次談話中這樣說道:“縈繞在我腦際的是禮貌之下的殘忍。人們將他們想要真正表達的意思隱藏在表面的語句下。我在小意大利的亞文化圈長大,當某人被殺時——這往往是一個朋友干的,可笑的是這種屠殺行為經常被弄得像一個儀式,一種獻祭。而在1870年代的紐約這一切都還不存在,那時的紐約是如此地冷漠。我不知道這兩種紐約哪一種會好些。”
《純真年代》是斯科西斯最偉大的電影之一,因為脫離了斯科西斯電影風格的主流而得不到欣賞,就像他的另一部影片《達賴的一生》(Kundun)一樣。斯科西斯在此片中展示了巨大的耐心,他讓永不停息的攝影機安靜下,而讓靜態的畫面來講述故事,而在表面安靜似水的畫面下卻隱藏著巨大的難以抑制的張力和節奏,上流社會的人全副武裝地在公共場合用訓練有素、精心打造的措辭彼此交談,性的沖動和壓抑在他們的心中翻滾洶涌,經歷過這些時刻的主人公們很難毫發無損地存活下來。而這正是影片所要表達的精髓。但在這一系列的反復和繁瑣中,仍然傳達出一種優美和尊嚴。
劇本精確地反映出小說原著的精神,斯科西斯在完美劇本的基礎上,配合專橫的攝影師Michael Ballhaus為影片裹上了一層社會學的包裝。為了更真實地還原出那一時代,影片在最微小的細節上都下足了工夫:精美的食物、高級雪茄、精致的織物、衣服、繪畫,直到適當的背景音樂。影片中的一切都是鑲金鍍銀的,充斥著水晶、天鵝絨和象牙。維多利亞時期的房間里堆滿了家具、繪畫、枝形大燭臺、雕塑、植物、羽毛、軟墊、古玩以及穿著和這一切相匹配衣服的人們。影片跳動著美麗的色澤,各種顏色在其中流暢地流轉。影片中的人似乎總在顧影自憐,而斯科西斯就用他那看似不動實則緩慢移動的攝像機不動聲色地破壞著他們的造型。攝像機移動得如此精巧以至很難察覺,靜止的攝像機或許是一種觀察,而移動的攝像機則就是一個觀察者。
《純真年代》的原聲由《我的左腳》的配樂大師、埃爾默·伯恩斯坦擔任配樂,為表現19世紀末上流社會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弦樂籠罩在古典樂怡人的氣氛當中。Dante Ferretti的舞臺設計和Gabriella Pescucci的服裝設計都是無與倫比完美無缺的,Michael Ballhaus的攝影則超越了他以前的水平。
表演
從最主要的角色到最次要的角色,演員們的表演都很到位。每一個表演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調整以保持一定的優雅來配合這場羅曼司的戰爭。素有“千面人”之稱的丹尼爾·戴-劉易斯這次照樣發揮出色,同劉易斯相比,維諾娜·賴德的表現沒有那么令人映像深刻,但在此片中,她的表演才能得到了比在《驚情四百年》中更好的發揮,并不需要扭緊雙手或是灑下眼淚,維諾娜·賴德扮演的梅是安靜端莊的,能輕易地融入背景,而這正是影片所要求的那樣。
關于伊迪絲·沃頓
本片根據伊迪絲·沃頓1921年獲得普立策文學獎的同名小說改編,她也是普立策獎歷史上首度獲獎的女性作家。
伊迪絲·沃頓是活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位重要女作家,1862年出生于紐約一富貴之家,幼年隨父母旅居歐洲,11歲回到美國。自幼受歐洲文化的濡染。伊迪絲少年時代即酷愛文學,1885年她與門當戶對的波士頓紳士愛德華·沃頓結婚,婚后一度中斷寫作。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滿。1907年她移居法國,1913年與丈夫離婚后定居巴黎,以全副精力投入創作。伊迪絲·沃頓與旅居歐洲的美國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亨利·詹姆斯對她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伊迪絲積極投入社會救濟活動,并因此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勛章。
1899年,伊迪絲·沃頓37歲時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高尚的嗜好》,從此進入小說創作的豐收時期,幾乎每年都有作品問世。1920年發表的《純真年代》代表了她小說創作的高峰。《純真年代》的主要情節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紐約上流社會,她將那一時代的紐約上流社會比作一個小小的金字塔,又尖又滑,很難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時隔40年后,沃頓在作品中又回到她曾經摒棄的過去,那個養育過她也束縛過她的社會,其感情是復雜的,其中既有親切的眷戀又有清醒的針砭。她試圖與這種過去取得某種和解。在經歷了世界大戰為人類帶來的血腥蹂躪之后,她重視審視了過去那個穩定的年代,期盼著一個既包含自我實現又是安全的隱定未來。《純真年代》被認為是伊迪絲·華頓結構技巧最為完美的一部小說。作家從自己親身經歷與熟悉的環境中提煉素材,塑造人物,將作品題材根置于深厚的現實土壤之中。尤其通過博福特命運浮沉這一線索與主人公愛情悲劇的主線相互映襯,使一個看似尋常的愛情故事具備了深刻的社會現實意義。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淡化人物社會行為、著力表現人物內心世界的嘗試無疑是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發展。而這一切使《純真年代》成為一部經久不衰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