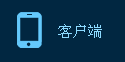他們管他叫“塌鼻子”,因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種外貌。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哈扎拉人的了解就這么多:他們是蒙古人的后裔,跟中國人稍微有些相似。學校的教材對他們語焉不詳,僅僅提到過他們的祖先。有一天,我在爸爸的書房翻閱他的東西,發現有本媽媽留下的舊歷史書,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書上的塵灰,那天晚上偷偷將它帶上床,吃驚地發現里面關于哈扎拉人的故事竟然寫了滿滿一章。整整一章都是關于哈扎拉人的!我從中讀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圖人(Pashtuns,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語言普什圖語為阿富汗國語)曾經迫害和剝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紀時,哈扎拉人曾試圖反抗普什圖人,但普什圖人“以罄竹難書的暴行鎮壓了他們”。書中說我的族人對哈扎拉人妄加殺戮,迫使他們離鄉背井,燒焚他們的家園,販售他們的女人。書中認為,普什圖人壓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前者是遜尼派穆斯林,而后者是什葉派。那本書記載著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師從未提及,爸爸也緘口不談。它還訴說著一些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比如人們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載貨蠢驢”等。我曾聽到有些鄰居的小孩這么辱罵哈桑。
隨后那個星期,有天下課,我把那本書給老師看,指著關于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幾頁,嗤之以鼻地把書還給我。“這件事什葉派最拿手了,”他邊收拾自己的教案邊說,“把他們自己送上西天,還當是殉道呢。”提到什葉派這個詞的時候,他皺了皺鼻子,仿佛那是某種疾病。
雖說同屬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鄰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里去了。據說她憎惡他的相貌,已經到了盡人皆知的地步。
“這是個丈夫嗎?”她會冷笑著說,“我看嫁頭老驢子都比嫁給他好。”
最終,人們都猜測這樁婚事是阿里和他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父親之間的某種協定。他們說阿里娶他的堂妹,是為了給聲名受辱的叔叔恢復一點榮譽,盡管阿里五歲痛失牯持,也并無值得一提的財物或遺產。
阿里對這些侮辱總是默默以待,我認為這跟他畸形的腿有關:他不可能逮到他們。但更主要的是,這些欺辱對他來說毫不見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經找到他的快樂、他的靈丹妙藥。那真是足夠簡單的事情,沒有產科醫生,也沒有麻醉師,更沒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儀器設備。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張臟兮兮的褥子上,身下什么也沒墊著,阿里和接生婆在旁邊幫手。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幫助,因為,即使在降臨人世的時候,哈桑也是不改本色——他無法傷害任何人。幾聲呻吟,數下推動,哈桑就出來了。臉帶微笑地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