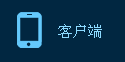許多世紀以來哲學家一直對語言與思維的關系頗感興趣。(61)希臘人認為,語言結構與思維過程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這一觀點在人們尚未認識到語言的千差萬別以前就早已在歐洲扎下了根。直到最近語言學家才開始認真研究與自己的母語截然不同的語言。兩位人類學家、語言學家佛朗茨•博厄斯和愛德華•薩皮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描述了北美和南美許多土著語言,在這方面他們堪稱先驅。(62)我們之所以感激他們(兩位無驅),是因為在此之后,這些(土著)語言中有一些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是由于說這些語言的部族或是消亡了,或是被同化而喪失了自己的本族語言。不過,在該世紀早期其他語言學家并不那么熱心處理“異域”語言中的怪異數據,因此他們常不被人們所稱道。(63)這些新近被描述的語言與已經得到充分研究的歐洲和東南亞地區的語言往往差別顯著,以至于有些學者甚至指責博厄斯和薩皮爾編造了材料。美洲土著語言的確十分特異,納瓦霍語實際上在二戰中可以被美軍用作密碼發密碼電報。
薩皮爾的學生本杰明•李•沃夫繼續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語言。(64)沃夫對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很感興趣,逐漸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在一個社會中,語言的結構決定習慣思維的結構。他論述說,某一特定語言中比較容易形成某些特定概念,但與此有別的其他概念則不易形成,因此該語言的使用者思考問題只會沿著這一條道而不會沿著那一條道進行。(65)沃夫進而相信某種類似語言決定論的觀點,其極端說法是:語言禁錮思維,語言的語法結構能對一個社會的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后來,這種觀點成為了知名的薩皮爾—沃夫假說,不過這個術語有點不妥。雖然薩皮爾和沃夫都強調各種語言之間的差異性,但薩皮爾自己從來沒有明確地表示過支持語言決定論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