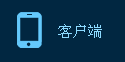還記得那個中心的教室不大卻很溫暖,休息室里有免費(fèi)的從中國代購的咖啡。Cazdyn老師講課時手勢飛舞,如施巫術(shù),云里霧里地講了半個小時,我瞪大眼睛看著他,他瞪大眼睛看著我,然后說,“這個你懂,這是馬克思主義,你從中國來怎么會不懂?”上完課寫完論文他請大家去他家里玩兒,我和同學(xué)趕緊偷窺他的寢室,我的天,三臺顯示器,一大堆空啤酒瓶,好吧,如果大家因此想起了我小說里的某些情節(jié),請?jiān)彙Uf到孟悅教授,UCLA的博士,當(dāng)年在大陸是女權(quán)主義批評的領(lǐng)軍人物,研究中國現(xiàn)代女性文學(xué)的學(xué)生不可能不看她和戴錦華教授合著的那本《浮出歷史地表》。孟老師是素食主義者,素到連代購來的雞蛋牛奶也不碰。有次找我談話,正碰上吃午飯,她拿出一盒菜問我,要吃不,我趕緊搖頭(心想多半就是沒煮過的生菜葉子)。
我的導(dǎo)師孫廣仁教授如此熱愛中國,年輕時學(xué)計(jì)算機(jī)的他,為追華裔女朋友奮而改行學(xué)中國詩歌,一直讀到哈佛大學(xué)的博士。他喜歡用大號回行針做書簽,聽他的課一旦不明白了,孫導(dǎo)馬上拿出一只筆:“太復(fù)雜了,我們畫個圖好不好?”我的另一位導(dǎo)師林理彰教授(中文名)是目前《老子》和《易經(jīng)》最權(quán)威版的英文翻譯者,他不僅譯了《周易》,連王弼的注解也全譯了。退休之后筆耕不輟,繼續(xù)譯《莊子》。老先生是嚴(yán)格的直譯派,聽他的課我們都膽戰(zhàn)心驚,因?yàn)榭傄沧g不對,他要求絕對忠實(shí)原作,翻譯的時候不到萬不得已,最好連主謂賓的位置也不要動。我把“攀龍附鳳”翻成“巴結(jié)”,他不同意,就得是“攀著龍,附著鳳” 大不了加個小注。
早年北美的中國學(xué)者都奮斗在翻譯的第一線,使得中國文化能以第二語言的外貌順利進(jìn)入英語文化圈,讓看不懂中文的學(xué)生們也能了解中國。后來導(dǎo)師帶著我和同學(xué)去哈佛東亞系開會,遇到著名的宇文所安教授,老先生穿一套亂七八糟的短袖T恤,叼一根福爾摩斯時代的煙斗,在臺上講“蘭花”這個詞在古文中的各種譯法,考證精確到植物學(xué)的地步,臺下聽眾全都癡了過去。大家也許不知,翻譯文言文,尤其是六朝時代的作品,絕對是件痛苦且考驗(yàn)人心的事。記得老師說,華盛頓大學(xué)的David Knechtges教授花了幾十年的功夫翻譯《昭明文選》,到了退休還沒有完工,心力交瘁他打算放棄,說想安度晚年。休息了一陣子又緩過勁來,撿筆頭繼續(xù)革命。中國文化的普及離不開這些在一線上勤奮耕作的學(xué)者,而各大學(xué)的東亞系為推廣普及東亞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
據(jù)說這次合并的原因是人文學(xué)院的巨大赤字,為節(jié)省行政開支,學(xué)校打算將東亞系、德語系、意大利、西班牙、斯拉夫語系及比較文學(xué)系合并成一個新的超級大系,取名為“語言文學(xué)學(xué)院”,而實(shí)力雄厚且代表加拿大官方語言的英文及法文系不在其中。北美的東亞研究早已不限于語言和文學(xué)這兩種,目前的主要區(qū)勢是跨文化跨學(xué)科的交叉研究。一旦降為語言文學(xué),系里有將近一半的教授,比如研究文化、歷史、考古、藝術(shù)、政治的教授們將被迫轉(zhuǎn)系。
東亞系作為傳承亞洲文化的核心將不再存在,這對于加拿大的東亞研究將是個災(zāi)難性的事件。這一舉措自然招致被合并單位的一致憤怒及抗議。作為東亞系研究生的一員我也響應(yīng)號召,將這個消息四處傳播擴(kuò)大影響,并希望對此事關(guān)注支持的同學(xué)們能在我們設(shè)計(jì)的抗議書上簽名。留下您的名字(拼音)、電郵即可完成電子簽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