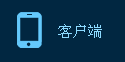來講一個我教師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早的棘手問題。那是1940年的1月,我剛從研究生院畢業,在堪薩斯城大學教第一學期的課。一個瘦高,長得就像頂上有毛的豆角架一樣的男生進入我的教室,坐下,雙臂交叉,看著我,好像在說:“好吧,教我些東西吧。”兩周后我們開始學習《哈姆雷特》,三周后他雙手叉腰走進我的辦公室,“看,”他說,“我來這里是想學做藥劑師的,干嘛必須要學習這些東西?”他沒有帶自己的書,就指著書桌上放著的我的書。
雖然我是個新老師,我本來是可以給這個家伙講很多事情的,我本想告訴他,把他招收來的不是制藥技術學校,而是大學,畢業時得到的學位證書是理學學士,而不是“合格的磨藥工”,這張證書證明他專修過制藥學,但它還可以證明,他還學到人類有史以來的一些思想。也就是說,他所上的不是一個技術培訓學校,而是一所大學,大學里學生可以得到培訓又可以得到教育。
我原本可以把這些話都講給他,可是很顯然,他不會呆多久,說了也沒用。
然而,我當時很年輕,責任感也很強,我就試著這么跟他說:“在你的余生中,”我說,“平均每天大約24小時,談戀愛時,你會覺得有點短,失戀時你會覺得有點長,但是平均的時間不變。其中大約8個小時你在睡覺。”
“每個工作日的其中八個小時,我希望,你會忙些有用的事情。假設你已經從藥科大學--或工程大學,法學院,或者其他什么大學--在這八個小時你要用自己的專業技能。作為藥劑師,你要確保氰化物沒有和阿司匹林混在一起,作為工程師,你要確保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作為律師,你要確保你的委托人沒有你的無能而處以電刑。這些都是有用的工作,它們涉及到人們都必須尊重的技能,它們會給你帶來基本的滿足。不管你做什么,它們可能是你養家糊口的本領。它們會給你帶來收入,但愿你的收入總能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