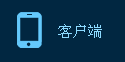在家門口,我凝視著23歲的兒子丹尼爾的臉,他的背包就放在身旁。他的背包就放在身旁。我們即將道別幾個小時之后,他就要飛往法國,在那里待上至少一年的時間。他要學習另一種語言學習法語,并在一個全新的國度體驗新的生活。
這是丹尼爾生命中的一個過渡時期,也是他從象牙塔進入成人世界踏出的一步。我希望送給他幾句話,幾句能令讓他受用終身的話語。
但我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們的房子坐落在海邊,此刻屋里靜寂無聲。屋外,海鷗在波濤澎湃的長島海域上空盤旋,我能聽見它們發出的尖叫。我就這樣站在屋里,默默地注視著兒子那雙困惑的眼睛。
更糟的是,我很清楚自己已經不是第一次讓如此重要的時光白白流逝。丹尼爾五歲的時候,那是幼兒園開學的第一天,我領著他來到校車的上落點。當校車在拐角處出現時,他的小手緊緊地攥著我,我感覺到了他的不安。校車到站那一刻,丹尼爾雙頰發紅,抬頭望著我——就像現在這樣。
爸爸,接下來會怎樣呢?我能行么?我會沒事嗎?說著,他上了校車,消失在我的視野里。車開走了,我卻始終開不了口。
十多年后,這一幕再次上演。我與妻子開車送丹尼爾到維吉尼亞州的威廉瑪麗學院讀書。抵達在學校的第一個晚上,丹尼爾和舍友們一起外出。次日清晨再見到丹尼爾時,他感到身體不適。其實當時他體內已出現白血球增多,但當時我們并不知道,以為他只是喝多了而已。
我正準備啟程回家時,丹尼爾正在宿舍的床上躺著。我很想說一些鼓勵的話語,在他的新生活伊始給他勇氣與信心。
但是,我再一次語塞。我只是咕噥了一句“希望你快點好起來,丹尼爾”就轉身離開了。
此時此刻,站在丹尼爾面前,我想起了那些被錯過的時刻。究竟多少次,我們讓這些珍貴的時刻白白溜走?例如兒子的畢業典禮,女兒的婚禮等等。我們疲于應付這些熱鬧的場面,卻沒有在人群中逮住孩子,找個安靜的地方,親口說出他們對我們有多么重要,或者與他們聊聊未來的人生。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1962年小丹尼爾出生于洛杉磯新奧爾良市。他比同齡人稍遲學會走路和說話,個子也長得不高。但是,盡管丹尼爾是班里最瘦小的一個,他性格熱情外向,人緣甚廣。由于協調性好且行動敏捷,他很快成為了運動高手。
棒球是丹尼爾人生的第一項挑戰。他是棒球隊里出色的投手。高三的時候,丹尼爾帶領學校棒球隊所向披靡,創下了七局五勝的記錄。在畢業典禮上,棒球教練宣布他為最有價值球員。
然而,丹尼爾最輝煌的時刻卻是在一次校園科技展上。丹尼爾帶著他的循環電路系統參加了這次展覽。與其他參展學生的那些新奇怪異、電腦操控、熠熠發光的模型相比,丹尼爾的作品相形見絀。我的妻子莎拉都替兒子感到臉紅。
后來才得知其他孩子的作品并非自己完成,而是父母代勞的。當評委在現場評審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些孩子都對參展作品一無所知,只有丹尼爾對答如流。于是他們把本次展覽的最佳作品獎頒給了丹尼爾,并授予艾伯特·愛因斯坦獎牌。
丹尼爾剛進大學時已經是個身高六尺,重一百七十磅的堂堂男子漢了。自從放棄棒球而選擇英國文學后,肌肉結實、身體強壯的丹尼爾卻再沒打過棒球了。我為他放棄了自己的體育特長感到惋惜,但更為他做出如此慎重的決定感到驕傲。
有一次,我告訴丹尼爾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誤就是大學剛畢業時,沒能抽出一兩年的時間周游列國。在我看來,這是開拓視野,形成豁達人生的最佳途徑。我成家工作以后,體驗異國文化的夢想就煙消云散了。
聽了這番話后,丹尼爾若有所思。丹尼爾的朋友告誡他說,為了游歷世界而把事業擱在一邊,這是非常愚蠢的。但丹尼爾并不認同。畢業后,他在大學校園端盤子,騎單車送報紙,還替人刷墻。通過打工掙錢,他攢足了去巴黎的路費。
丹尼爾離開的前夜,我在床上輾轉難眠。我想準備好明天要說的話,但腦袋里卻一片空白。也許根本就無須贅言,我安慰自己。
即使一位父親一輩子都不曾親口告訴兒子自己對他的看法,那又如何?然而,當我面對著丹尼爾,我知道到這非常重要。我愛我的父親,他也愛我。但我從未聽過他說心里話,更沒有這些感人的回憶。為此,我總心懷遺憾。現在,我手心冒汗,喉嚨打結。為什么對兒子說幾句心里話如此困難?我的嘴唇變得干澀,我想我頂多能夠清晰地吐出幾個字而已。
“丹尼爾,”我終于迸出了一句,“如果上帝讓我選擇誰是我的兒子,我始終會選你。”
這是我惟一能想到的話了。我不曉得丹尼爾是否理解了這句話,但他撲過來抱住了我。那一刻,世界消失了,只剩下我和丹尼爾站在海邊的小屋里。
丹尼爾也在說著什么,但淚水已經模糊了我的雙眼,我一個字也沒聽進去。只是當他的臉向我貼過來時,我感覺到了他下巴的胡子茬。然后,一切恢復原樣。我繼續工作,丹尼爾幾個小時后帶著女友離開了。
七個星期過去了,周末在海邊散步時我會想起丹尼爾。橫跨拍打著這個荒蕪海岸的茫茫大海,幾百英里之外的某個地方,丹尼爾也許正飛奔著穿越圣熱蒙大道,或者在羅浮宮散發著霉味的走廊上徘徊,又或者此時正托著下巴坐在左岸咖啡館里憩息。
我對丹尼爾說的那些話既晦澀又老套,空洞無文。然而,它卻道出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