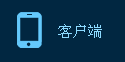或許,是你的遺傳密碼讓你那么做的。
不論你最近在投資方面犯了什么錯誤,很可能是因為你有某種跟這些行為有關聯的基因。你是否注定要成為自身基因密碼的奴隸呢?
為揭開這個疑問,最近我在匹茲堡大學花了一天時間,接受了大量DNA分析和大腦掃描。我自認為還算是一名耐心且懂得節制的投資者,因此,我自告奮勇在哈里里(Ahmad Hariri)的基因成像實驗室充當人類“小白鼠”,以便了解我的基金和大腦活動對我行為的影響。結果讓我大吃一驚。
我在一個杯子里留下唾液樣本之后,哈里里就開始進行分析,以便找出影響我大腦中負責風險和回報決策回路的5種基因屬何種形態。他的分析結果是:在這5種基因中,我都存在有時與不良投資決策相關聯的對位基因。
比如FAAH基因。在歐洲血統的人群中,大約25%的人攜帶這種基因的385A對位基因。這種基因往往會抑制他們大腦的恐懼回路,加劇大腦對賺錢前景的反應。我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
再看看DRD2基因。大約20%的白種人攜帶一種會讓他們對賭博作出較激烈反應的對位基因,即使他們并不懂賭博技巧。這種基因我也有。
在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儀(fMRI)對我的大腦進行掃描之后,得出的圖像也不是很理想。
當我躺進造影儀的艙里,我看到一張底朝下的卡片,然后我需試著估計它的高度與一張5美元的鈔票相比是大還是小。如果猜測正確率足夠高的話,我就可以得到10美元。每當我猜對的時候,我的大腦紋狀體(這是大腦的反饋中心)的反應強度是哈里里醫生對一般人所得試驗結果的兩倍左右。
這表明,我對賺錢的本能沖動比其他投資者要強很多。哈里里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往往渴望立刻賺到錢。哈里里說,“控制這種對回報的沖動反應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非常重要”,比如在投資方面,沒有耐心常常會降低回報。
另一項測試表明,我的大腦對恐懼的敏感度比接受哈里里試驗的一般人要高出50%。
總起來看,我的遺傳標志和大腦活動特征似乎生來注定要招來投資災難。
令我欣慰的是,實驗室還就我對現實世界財務決策的反應情況進行了測試。結果卻不同。
給我的問題是:是選擇早些得到較少的利潤,還是晚些得到較多的利潤?許多人不喜歡等待,會選擇今天就拿到50美元,而不是一年后拿到100美元。我的選擇是要么是一年后得到100美元,要么是今天拿到不少于90美元。哈里里看到這個結果后開玩笑說,我簡直“像禪宗一樣富有耐心”。
我的原始基因與我最終行為之間的反差高得不尋常。每個人的冒險偏好度或許有20%從遺傳上說是先天決定的,其他則來源于我們的成長過程、經歷、教育和訓練。因此,盡管我的基因使得我的大腦容易大驚小怪,而且傾向于迅速賺錢,但我的實際行為卻并非如此。我會持有某項投資達數年乃至數十年;我對熊市并不恐慌,牛市卻會讓我感到不舒服。
現在我終于知道,這些習慣并非我天生就有的。多年來我一直在跟我的基因作斗爭。在我的一生中,我大腦的反射功能一直試圖控制我的情感。
我從小在農場長大,慈愛的父母對歷史很了解,或許他們當年培養了我用長遠眼光來看待暫時的變化,不要沖動,三思而行。通過研究格拉罕姆(Benjamin Graham)和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著作和經歷,我學會了不要盲從他人,并記住未來的回報取決于今天的價格。
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天性和后天教育之間永遠在相互較量。但是哈里里說,在目前這樣的恐慌時刻,“環境壓力可能會在相當程度上讓你由基因決定的內在傾向暴露出來”。換句話說,熊市之下本能將占據上風。現在這個時候,堅持讓自律控制你的基因沖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但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