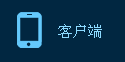我環顧周圍,房間發生的變化微妙卻又明顯。墻壁上排列滿長著細腿的大象,我四周的人都已變成了巨大的昆蟲,我的手表熔化了,從我的手腕上慢慢地往下滴落。難道是達利式的夢?或者是卡夫卡式的噩夢?超現實主義的微風撩動著我的頭發;存在主義的旋風俘獲了我的想像力。
從這兩位偉大創作者筆下的形象之中,我看到了其反射出的美麗的和永不滿足的想像力,全然不守成規、狂放不羈,然而又充滿了藝術家洞察力的神奇和力量。這些形象不如照片那么真實,但是又比照片可信一百倍。我也常常發現自己曲解了這個世界。在聽那些著實乏味枯燥的講演時,我有時對正在學習的東西打幵想像之門,使自己保持清醒;我所看到的并不是老師繼續講的美國內戰中的戰役,而是看到高舉的旗幟下步槍在射擊。
更多的時候,我把自己的生命視為一次冒險,極富傳奇色彩,而且又理想化,令人激動振奮。在我眼中,令人厭倦的記憶力測試變成了對于意志力的檢驗;辯論變成了智慧之戰;生活的畫卷變成了人類與命運之神對抗的存在主義的,令人癡迷的戰爭。在這些畫面里,有時我會遭遇無形的敵手的挑戰,有時我又在登山。或許我正在和一頭公牛鏖戰,或許正在屋頂上跳來蹦去。
我時常會想,如果世界變為我想像的模樣,將會有什么裨益。當然,每個人都確實這么想過。即使最嚴謹的思想家也會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設想。達利和卡夫卡也不例外,他們是極端的情況。為何我們都如此渴望逃離現實?我發現自己像許多人一樣,經常看起來不太厲于這個世界。但是當然我又是屬于這個世界的,因為這個世界是我的,就像它也是其他任何人的一樣。我試圖通過對這個世界作出細微的變動來解決感知與真實之間的矛盾馬車代替了小轎車,獲獎的散文代替了家庭作業以便世界在我身邊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真是個簡單的解決辦法。我們并不是改變自己來適應這個世界,相反,我們改變世界,以讓它適應我們。就靠簡單的心愿之旅,一切都可以做到。當然,用意識熔化手表遠比被手表束 縛住才智好得多,后者就像精靈被瓶子困住手腳一樣。思想的自由并不要求太多;調整世界,使之適合我們的思想,要比調整 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世界高貴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