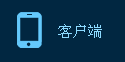我的前公爵夫人墻上的這幅面是我的前公爵夫人,看起來就像她活著一樣。
如今,我稱它為奇跡:潘道夫師的手筆經一日忙碌,從此她就在此站立。
你愿坐下看看她嗎?我有意提起潘道夫,因為外來的生客(例如你)凡是見了畫中描繪的面容、那真摯的眼神的深邃和熱情,沒有一個不轉向我(因為除我外再沒有別人把畫上的簾幕拉開),似乎想問我可是又不大敢問;是從哪兒來的——這樣的眼神?
你并非第一個人回頭這樣問我。
先生,不僅僅是她丈夫的在座使公爵夫人面帶歡容,可能潘道夫偶然說過:“夫人的披風蓋住她的手腕太多,”或者說:“隱約的紅暈向頸部漸漸隱沒,這絕非任何顏料所能復制。”
這種無聊話,卻被她當成好意,也足以喚起她的歡心。
她那顆心——怎么說好呢?——要取悅容易得很,也太易感動。她看到什么都喜歡,而她的目光又偏愛到處觀看。
先生,她對什么都一樣!她胸口上佩戴的我的贈品,或落日的余光;過分殷勤的傻子在園中攀折給她的一枝櫻桃,或她騎著繞行花圃的白騾——所有這一切都會使她同樣地贊羨不絕,或至少泛起紅暈。
她感激人.好的!但她的感激(我說不上怎么搞的)仿佛把我賜她的九百年的門第與任何人的贈品并列。誰愿意屈尊去譴責這種輕浮舉止?
即使你有口才(我卻沒有)能把你的意志給這樣的人兒充分說明:“你這點或那點令我討厭。這兒你差得遠,而那兒你超越了界限。”
即使她肯聽你這樣訓誡她而毫不爭論,毫不為自己辯解,——我也覺得這會有失身份,所以我選擇絕不屈尊。
哦,先生,她總是在微笑,每逢我走過;但是誰人走過得不到同樣慷慨的微笑?
發展至此,我下了令:于是一切微笑都從此制止。她站在那兒,像活著一樣。請你起身客人們在樓下等。
我再重復一聲:你的主人——伯爵先生聞名的大方足以充分保證:我對嫁妝提出任何合理要求都不會遭拒絕;當然.如我開頭聲明的,他美貌的小姐才是我追求的目標。
別客氣,讓咱們一同下樓吧。但請看這海神尼普頓在馴服海馬,這是件珍貴的收藏,是克勞斯為我特制的青銅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