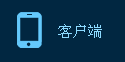父親送給我氣槍的那一天正是我12歲的生日。看到獵槍的那一時刻,我高興得差點兒跳了起來。帶著微笑,父親將我領(lǐng)到屋外,告訴我該如何射擊---先裝上子彈,壓幾回氣,然后瞄準,最后射擊。把獵槍遞給我之前,父親一板一眼地說道,“我可不想讓你殺害生靈。這可不是我給你買這枝槍的初衷。”我想他是怕我已經(jīng)知道真正的權(quán)力意味著什么。不管怎樣,這對我來講倒也沒有什么關(guān)系,因為我知道會有許多別的東西可以成為靶子。
“嘿,邁克。”我大聲喊著我朋友的名字,發(fā)現(xiàn)他我真是喜出望外。“看著點兒。”我舉槍瞄向了電話線桿的頂部。“你在干什么?”他問道。我開了一槍,子彈擊中了電話線桿的頂部,發(fā)出“叮當”一聲響。“太棒了。”邁克說道。我像一位世界之王似地笑了。當邁克沒能擊中同一目標的時候,我笑得越發(fā)地得意了。射擊這樣的目標的好處是不管你打了幾槍,目標永不會破損。你便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射擊。可也許正是因此,它開始變得乏味了。
幾個月之后,我沿著街道走著,手中提著那枝槍,搜尋著新的目標。在一個電話線桿的前面我停下了腳步,百無聊賴地隨便地放了幾槍。忽然間,一只小鳥輕巧地落在了電線上。那是一只鴿子。它咕咕地叫著并左右不停地移動。這一切都盡收我的眼底。這里的我正無所事事,手中提著一枝氣槍,而眼前的不遠處則落著一只鴿子。沒有人會告訴父親。太妙了。我心想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于是,我瞄準了那只鴿子,屏住呼吸,慢慢地開始扣動扳機。就在子彈即將出膛的一瞬間,我一下子猶豫了。我就要射殺一只小鳥,這個念頭令我感到很不安。然而與此同時,興奮之情卻占據(jù)了我的另一半心房。終于后者戰(zhàn)勝了前者。
我開了槍。那只鳥像一塊石頭一樣落了下來,墜落中它的一只翅膀還在不停地撲騰著。由于草叢的遮擋,我沒有目睹它是如何落地的,但是我卻聽到了它摔在土里發(fā)出的撞擊聲。槍尚未放下,我便意識到我做了什么---我第一次親手殺害了一只動物。我本可以跑到朋友邁克家,把他拉去看看那只死鴿子。但是,我想不能這樣做,于是暗叫了一聲“啊,不”,便一頭沖進了樹叢。此時我心亂如麻,嘴中祈禱道,“啊,上帝,請不要讓它死去。”那只鴿子躺在那里,鮮血從嘴中不停地涌出來,大大小小的羽毛散落一地。我用槍托捅了捅它,但它沒有任何動靜。我伸手將它翻過身,可它的腦袋卻毫無生機地耷拉到了一邊。我掩埋了鴿子,匆匆地趕回了家。我悄悄地將氣槍藏進衣櫥,然后躲到了自己的房間。
當父親晚上回家時,我強打著精神下了樓,這樣他就不會起疑心了。然而當父親第一眼看到我時,我敢發(fā)誓他對所發(fā)生的事情已經(jīng)一清二楚了。他用胳膊摟住我,問道,“兒子,你今天過得咋樣呀?”“嗯,還行。”我告訴他。“就這些嗎?”我皺了皺眉頭,“只是還行嗎?”我感到我的臉燒得很。“是呀,就是還行。”我聳了聳肩,至少讓他能相信我一半。父親點了點頭,手依然搭在我的肩膀上。“好吧,”他說道,“快要到吃飯的時間了。咱們一起擺桌子去吧。”
我把碟子拿出來擺放時一聲未吭。每次轉(zhuǎn)過身,我都似乎感到父親的目光在盯著我。而每次我偷窺他時,他卻又似乎在小心地收叉子、擺酒杯。父親為我倒了點牛奶,然后坐下,我僅以一句“謝謝”敷衍了過去。望著他,我想如果我能熬過這頓晚飯,便算過關(guān)了。母親為我們每人遞上一塊土豆,并將餐桌中央的主菜掀開了蓋兒。那是一只雞。我差一點將飯吐到了盤子中。我瞧了一眼母親,又瞅了瞅父親。在淚水還沒有涌出眼眶之前,我把椅子往后一推,然后跑回了自己的房間。我將頭埋在枕頭里。這時,我感到父親正撫摸著我的后背。淚水慢慢地干了。我抬起了頭。父親什么也沒有講,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身上,用一種溫柔的目光期待著我。
“我……,”我講不下去了,清了清嗓子,說道,“我今天殺死了一只小鳥。”“噢?”父親哼了一聲,而表情卻沒有任何變化。“是的,那是一只鴿子,落在電話線桿上,我射死了它。”父親停了一會兒,問道:“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呢?”“很……很不好受。”我答道,低下了頭。
“肯定是這樣的。這正是我告訴你不要射殺鳥類的原因之一。”我望著他:“你要狠狠地罰我嗎?”
“嗯,”他將手指壓在嘴唇上答道,“你把你的氣槍用在不該用的地方,又不聽我的話。你要做的就是永遠記住,射殺一只可憐的小鳥之后的感覺是多么糟糕。”我的頭又一次垂了下去,可是父親卻用手指托起了我的下巴,直到我的目光與他的相遇。“不管怎樣,”他說道,“我想你會記住的。”然后他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屁股:“現(xiàn)在咱們一塊去吃晚飯吧。”
當我從床上滑下的時候,我并沒有領(lǐng)悟到父親的話該是多么地正確。是的,這一生,我會像記住許多其他事情一樣,永遠牢記我曾射殺了那只小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