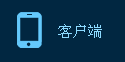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中文譯文】
最好的圣誕節禮物
我對圣誕節最深刻的記憶總是和一只小貓聯系在一起。我第一次見到它是我出診去給安斯沃思太太的一只狗看病。我有點驚奇地瞧著蹲在爐前的那個毛茸茸的黑色小生靈。“我還不知道你有只貓,”我說道。
那婦人微笑著說:“我們沒有貓,這是戴比,至少我們這么叫它。它沒主,一個星期來兩三次。我們給它點吃的。我不知道它住哪兒,可我相信它在沿路的一個農場附近待過很長時間。”
就在我注視戴比的時候,它轉過身,靜悄悄地出了客廳走了。“戴比總是這樣,”安斯沃思太太笑道。“它從來就只待10分鐘左右,然后就走了。”
安斯沃思太太40多歲,微胖,慈眉善目。她是那種獸醫外科醫生理想的客戶---富裕、慷慨、3條受寵的短腿獵犬的主人。這幾條獵犬慣常就是憂傷的表情,只要有一條加重了一些,我就得火速趕到她家。
所以,雖然我經常去安斯沃思太太家出診,但都不是非急不可的,我總有足夠機會留心觀察那只激起我好奇心的小貓。有一回,我發現它津津有味地在小口吃著廚房門旁碟中的食物。我注視它時,它轉過身來,踩著輕步,幾乎是飄游進過道,然后穿過客廳門。那3只短腿獵犬已經四肢舒展地躺在壁爐邊的鋪墊上呼嚕呼嚕地睡覺了,但它們看來很習慣戴比。
戴比以慣常的姿勢蹲在3只狗中間---挺直、專注、目不轉睛地盯著燃燒的煤塊。這回我試著和戴比建立友誼。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它,可我伸出手時,它卻俯身避開了。然而,我耐心地說了一番甜言蜜語后,終于摸到了它,并用一個手指輕柔地撫摸它的面頰。戴比把頭歪向一邊,蹭著我的手,但很快它就起身要走了。戴比一出屋就沿路飛奔,然后穿過樹籬一處空隙,最后只見那小黑影輕快地在雨淋過的草地上一掠而過。
我再次和安斯沃思太太有聯系必是在將近3個月以后了。實際上,她來電話前,我已經感到奇怪,這么長時間她那3只短腿獵犬竟然一點病癥也沒有。
那是圣誕節的早上,安斯沃思太太道歉說:“赫里奧特先生,我非常抱歉偏偏在今天打攪你。我想你跟別人一樣今天也該休息。”但是這些隨口而出的客氣話未能掩飾她話語中的不安。
“請不必擔心,”我說道。“這回是哪一只?”
“哪只狗也不是,是……戴比。”
“戴比?她此刻在你家嗎?”
“在……可有點不對勁。請馬上來。”
安斯沃思太太的家鋪張地用金銀箔和冬青裝飾著,餐具柜上擺著成排的酒水,火雞和撒爾維亞干葉加蔥頭填料的濃郁香味自廚房撲鼻而來。但是,安斯沃思太太領我進客廳時,她眼中充滿了痛苦。
戴比是在客廳里,但是這回情形完全不同。它沒有像平常那樣挺直地蹲著,而是側身四肢伸展著一動不動,緊靠它身旁躺著一只小黑貓。
我困惑地朝下看。“這兒出了什么事?”
“真是再奇怪不過了,”安斯沃思太太回答說。“我已經有幾個星期沒見過它了。大約兩個鐘頭前它進來了,有點瘸拐地進了廚房,嘴里叼著那只小貓。然后又叼著它進了客廳,把小貓放在鋪墊上。開始時,我覺得挺逗樂。可是我能意識到很不對勁,因為雖然戴比像平常那樣蹲著,可是這回蹲了很長時間---有一個多小時---后來就這么躺著,再也沒動過。”
我跪在地毯上,用手摸戴比的脖子和肋骨。它比以前更瘦了,毛很臟還粘著泥塊。我輕柔地掰開它的嘴,它沒有拒絕。喪鐘在我腦海里敲響。
安斯沃思太太的說話聲像是從遠處傳來。“赫里奧特先生,它病了嗎?”
我支吾地回答說:“是的……是的,我想是病了。它長了個惡性腫瘤。”我站起身來。“我很抱歉,你絕對是無能為力了。”
安斯沃思太太伸出手舉起那在泥水中拖臟的小黑貓仔,用手順著沾滿泥的毛撫摸著。貓仔的小嘴張開做喵叫狀,但卻沒有聲音。“是不是有點怪?戴比活不長了,可它把它的孩子帶到這兒來,而且是在圣誕節這一天。”
安斯沃思太太面頰上的淚珠已經干了,望著我,目光明亮。她說道:“我以前從沒養過貓。”
我微笑著說,“看來你現在有一只了。”
她確實就有了貓。小貓仔很快長得渾身油亮、漂亮,生性調皮,由此贏得“歡鬧鬼”的稱號。我每次去安斯沃思太太家時,都懷著喜悅的心情看著“歡鬧鬼”慢慢長大。
我看著它,一副活潑健康、心滿意足的樣兒,不禁想起了“歡鬧鬼”的媽媽。那臨終的小生靈用殘存的最后一點力量,把自己的后代帶到它所知道的惟一能獲得溫暖和舒適的地方,希望孩子能得到照料。是不是我想得太多了?也許是的。
但是,看來有這種想法的不止我一個。安斯沃思太太轉向我,雖然微笑著,可眼中流露出思念之情。她說,“戴比會感到高興的。”
我點頭稱是。“是的,它會的……正好一年前它把‘歡鬧鬼’帶來的,不是嗎?”
“沒錯。”安斯沃思太太又緊抱住“歡鬧鬼”。“這是我有過的最好的圣誕節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