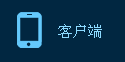星期日的上午總是這樣。一覺醒來, 最先感到的是躺在妻的空枕上。我幾乎還能嗅到她的芬香, 而我的雙手急切地伸出要去觸摸她的軀體。這就是她離我而去時在我心中留下的感受。帶著這般心情, 我懶洋洋地用握緊的拳頭揉了揉睡眼, 然后雙手撓了撓蓬亂的頭發, 強打著精神下了床。慢慢地站起身, 我聽到了樓下的電視機里飄來“Bullwinkle and Rocky”節目的聲音-很明顯, 安杰爾已經醒了。這個時候, 我的臉上總能感受到一絲笑容。我徑直走下樓梯, 緊緊地抱住她, 吻她。每日我倆都重復著同樣的儀式。但有時我太疲乏了, 就會把這一切忘了。這時, 安杰爾總會對我甜甜地噘起雙唇, 期盼著我的回應。“你在干嗎?”我總是這樣問她。“現在是早上, ”她答道, 隨之又把嘴唇鼓起。“我知道是早晨。但是你究竟在干什么呢?”
當然, 答案我是再清楚不過的了。這時, 安杰爾總會以一個3歲孩子所特有的可愛樣子大聲地嘆口氣, 并翻翻眼珠子。“爸爸, 我在等你親我呢。”于是, 我彎下身, 盡職地, 而又帶點兒懊惱地吻一下她那嬌小的雙唇。這必然會使她臉上綻出她那比朝陽還要明亮的笑容。
與安杰爾共進早餐是一天中我最快活的時光。我的妻, 一個真正的夜貓子, 周日不 到正午是絕不會醒來的。所以我們只有各顧各的肚子了。最近, 我已練成了一個不賴的廚師了。我們的桌子上通常擺滿了薯條、熏肉、肉桂松餅、鮮橙汁, 還有咖啡。安杰爾和我的話題不外乎是她的娃娃以及她一天的安排。大多數時間是在玩“過家家”, 還有吃零嘴兒。我攤開報紙, 指給她看所有的圖片, 并把相關的故事講給她聽。“跟電視沒什么兩樣。”她大喊起來;我笑著搖搖頭。
吃完飯, 安杰爾和我便開始了每日的穿衣儀式。這一過程她定要獨立完成。我仔細地看著她, 并在她萬一系不上扣子時幫上一把。星期日需要衣冠楚楚。安杰爾對此很不情愿, 因為這使得她在室外玩耍很不方便, 但是她從不抱怨。她清楚為什么她要穿戴整齊。我將衣服披上身, 然后鉆進了汽車, 開始系安全帶。“誰最后系上誰是臭蛋。”安杰爾喊道。于是我倆便爭先恐后地把安全帶系上。這已成為我倆一定要玩的游戲。于是我們便開始了駛往墓地的路程。
穿梭于墓碑與鮮花之間, 安杰爾開始變得沉默寡言。這里是父親的傷感之地;她本能地曉得不能喋喋不休地亂說話。對她的沉默我很感激。這使我得以沉浸于傷感之中。這里是妻現在的長眠之地。
卡麗·羅切爾·戴維斯
邁克爾的愛妻、安杰爾的慈母
生于1966年5月2日
歿于1995年7月1日
堅硬的、灰暗的碑石如是說。碑文就是如此嚴苛率直, 即使是深夜閉上眼, 我也能看見它們。
環繞我們的是春天的氣息。樹林已是枝綠葉茂。我聽到了孩子們在院子中嬉戲的聲音;我還聽到了綠地上割草機的轟鳴聲。空氣中洋溢著和煦的微風---它拂暖了你臂膀上的汗毛。
然而, 這一切都不是卡麗。耳后散發著香草芬芳的卡麗, 有著寒空中冰藍的雙眸的卡麗, 隨著車內高音量的樂曲哼唱走調的卡麗。這是塊死般靜的地方, 它不是卡麗。我的卡麗會笑我如此癡心的。她定會希望我重新開始我的人生, 找一位我可以向她付出愛的女人的。然而, 每一個周日我們依舊來到這里。
安杰爾雙膝跪著, 凝視著我放在地上的那束桔黃色的郁金香。“媽咪喜歡花兒嗎?”她問道。“是的, 寶貝。她喜歡最鮮艷的花兒。這些花兒使她開心得很。”說這話時淚水直在我的眼眶里打轉。我強忍住眼淚。然而, 在我覺得剛剛要平靜下來時……
“媽咪什么時候回家呀?”我一下子心如刀絞, 沒有回答她。看到我的樣子, 安杰爾不禁用柔弱的雙臂摟住了我的腿, 說道, “好了。那, 那讓我們跟媽咪道聲晚喃(安)吧。”我默默地點了點頭。安杰爾隨后起了身。
“媽咪, 再見了。當心別讓蟲子給叮了。”她拍一下墓碑頂部, 就像在拍一只愛犬的腦袋。我不禁笑了。對于她, 這里將永遠是媽咪的睡榻, 而爸爸則不斷地將束束鮮花放在她的床邊。安杰爾永遠也不會了解這個將她從醫院抱回家的女人, 也不會曉得這個女人曾經整個晚上泣不成聲, 只因為“她總有一天會長大、上學, 然后戀愛、嫁人, 而我則成了一個老奶奶。”這樣想著, 一絲微笑不知不覺地掛在了我的嘴角。“過來吧, 美妞兒。我們一起回去玩過家家吧。”“那我能做媽咪嗎?好嗎?!”“當然可以了”。于是我倆轉身離開了墓地, 一同去迎接下午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