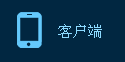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你認為會發生什么呢,喬更斯?”一天在酒吧里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問道。
“發生什么?”喬更斯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以前,人們對別的國家想干什么,以及他們的能力都持有懷疑。但現在完全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呢?”這個人問。
“因為現在有了許多發明,”喬更斯答道,“對此我們一無所知,既然一個人可以在包里放上一個威力比數艘戰艦還大的炸彈,那么就很難去弄清一個國家能做什么或是以后會干什么。我可以給你們舉一個例子。”
在熱帶我乘坐的船(喬更斯告訴我們的)駛入一個港口。我討厭總看熱帶海,于是上了岸,走進一家小酒館,看看那里賣不賣這個國家的好酒。結果卻沒有。但酒吧有一個人,留著黑色的小虎子,眼神里有一種特別的東西讓我覺得他可能有有趣的事情要講。所以,我問可不可以請他喝一杯酒。他欣然接受了,于是我叫了一瓶當地奇特的酒,打開瓶塞后倒出的酒就像液化的熱帶陽光一樣,很烈。我看著酒從他的黑胡子下汩汩而進。幾杯酒下肚后,他開始侃侃而談。
“我們的目標是控制整個加勒比海地區,”他說道,“你可不要以為我們是個小國家,就不能成功實現這一點。戰爭不再是軍隊的比拼;它的勝負取決于科學家的智力。而我們就有一個已被我證實的在拉丁美洲找不到的頂尖科學家。”
“你證實的?”我不禁問道。
“是的,”他說道,“你好好聽著。”
我又給他叫了一瓶酒,聽他講故事。
“你可能想不到,”他說,“我以前在國防部干過。”
我確實沒有想到這個,因為他與一個戰士的形象相距甚遠。但是戰爭如他所說的那樣,已經發生了變化。
“我們的部長,”他說,“是個騎兵隊指揮官,思想適應不了現在科學。他把戰爭簡單地看成是獲取部隊指揮權、身穿精美制服和博得榮譽的手段。我們不得不除去他,才能實現我們正義的抱負。”
“什么抱負呢?”我問。
“就是對整個加勒比海地區的控制權,他答道,“這是正義的事業,是我們民族的天職。”
“當然,”我安慰道,雖然我并不知道他所說的這個民族指的是哪個國家。
“國防部長下臺后,”他繼續說,“我們將注意力轉向現代戰爭,并開始取得巨大的進步。現代戰爭使小國家獲得了天賜良機。以前,如果一個國家有十二艘戰艦,就算是非常強大了,我們只能服從它。但是如果我們知道怎樣釋放一場足以摧毀所有國家的瘟疫,那又會發生什么事情呢?我們還要對我們正義的志向保持沉默嗎?不。我們應該講出來。”
“當然,”我說道。
“其他國家知道一點細菌戰的技術,”這個陌生人說道,“我們則尋找新的更致命的細菌,并且還懂得如何更有效地傳播細菌。有個人不僅可以為我們提供這種細菌,還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傳播這些細菌---他名叫卡拉希爾拉。我們知道,只要卡拉希爾拉能堅持工作的話,我們就可以獲得驚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