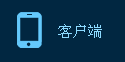春之祭--亞瑟.米勒
我從來都不明白我家為什么會開辟一方菜園,也不明白為什么36年前我在鄉下買下有生以來的第一處房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開墾一塊地來種菜。相對來說,買把胡蘿卜或甜菜容易且便宜,這我是知道的,但是為什么還要種菜呢?尤其是塊根蔬菜,商店里買的和自己種的并沒什么區別。人的本能是想做點什么事,這是一種從祖先那里遺傳來的本能,讓我愿意不辭辛勞地著迷于勞作。另外,我并不是很喜歡吃蔬菜,更愿意吃多汁油膩的東西,比如熱狗。
現在,如果可以在窗外種些熱狗,我當然毫不猶豫地托出其正當的理由來。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每當四月來臨,我會不自覺地倚在籬笆上看著這片可憐的菜地,用盡所有理性的力量去勸說自己不要再種了。但是有個早上不可避免地來了,那天我剛醒,就聞到窗外飄進的一縷香氣,空氣中有種泥土的氣息,這香氣仿佛從地球的最核心的地方飄來。突然,太陽異樣的深黃色的光照到毯子上,我感到是該種點什么的時候了。小鳥開始歇斯底里地鳴叫著,她們跟我都想到了--蚯蚓正在松散的泥土里津津有味地掘土。
我欣喜地看著這塊土地,但是心里也充滿了矛盾。每年的難題都一樣---用什么方式種呢?前幾年我用的是36寸寬的黑色塑料膜,成效不錯,干旱的時候土壤仍能保持水分,不生雜草。
但是黑色塑料膜看起來太工業化、太不浪漫了,我開始慢慢用雜草來覆蓋。我們收割了很多干草,干草腐爛后確實能改良土壤成分,而且看上去也很可愛,而且不用花錢。
照顧菜園可以讓人意識到如何精巧、慷慨、容易地糟踏這個小星球的表面。這塊50英寸寬、70英寸長的田地必須得有十幾種不同的土壤。西紅柿不能在只有一種土壤的田地生長,也需要別的土壤,別的作物也是這樣。如果施以化肥,我想這種區別就不那么明顯了,但是我用化肥很節儉,只是在播種種子的那些行列,而不是播撒在整片地里。我這樣不是為了節省化肥,也不是不愿意幫助雜草,我不明白自己為什么這么做。
我覺得,至少對于一定的園藝者來說,園藝的樂趣是神經和精神方面的。不管什么時候,當你感到生活沒有意義,很難把握,你就可以走進菜園做些什么;無助的生命依賴你,需要你的調理和鼓勵,需要你的保護以免受敵人的攻擊,這時你心中的父愛或母愛的本能就會自然流露。有時候,菜豆和黃瓜會像孩子一樣,大量地出現在你面前,每天早上都會結出越來越多的果實來,跟著你、威脅著用它們的藤蔓勒著你。
園藝也是項精神性的工作,你總是從春天開始就想辦法讓它在這一年里都看起來干凈整齊,像排列整齊的圖畫那樣。但是到了七月,你再一次看到了熱鬧景象:豐腴的胡蘿卜、萵苣和甜菜。這個時候,我的妻子---菜園的女主人露面了。她喜歡吃大量的蔬菜,她剔除掉多余的幼苗,用手耕作著。她耐心地蹲在那里,決定著哪棵應該長著、哪棵應該扔到一邊。
大約這個時候,我妻子86歲的老母親--一位植物學家--首次造訪菜園。她懷疑地四下看看。她最喜歡做的工作就是把西紅柿苗綁到木樁上。這是個直率、真誠的婦人,或者說了解
真相后是這樣。這會兒,她沒有說,“你們把西紅柿種在菜園的潮濕處了,”她會等到十月,這時候她會開始每年一次回歐洲家鄉的旅行,她會向我吻別,并不經意地說,“種在濕地的西紅柿容易感染真菌,”然后走上飛機。但是直到十月菜園里一點兒問題都沒有,我堅信我以后再也不會種它了。
我想,我種菜是因為我必須要這么做。每天幾次都得走過荒蕪的用籬笆圍住的菜園,這是件難以忍受的事。做這件事是可以得到補償的,讓我每年都將注意力傾注在勞動上。早上七點鐘,陽光下的菜園閃閃發光,一切都濕濕的、閃耀著,叢中一片片的蔭影,沒有什么場景能與之媲美。事實上,這比一排排的熱狗可愛多了。內心孤獨的一隅甚至用這一景象來自我安慰,所有這一切都健康地生長著,這秩序井然、蓬勃的生命一定不自覺地反映了人的內在精神。沒有這么個菜園來經營、種植,我不知道四月份有什么意義。
四月意味著再一次在這種無意義又耗時的愛好上惹自己生氣,我不理解那些聲稱“喜歡”園藝的人。菜園是一個人自我的延伸,是以別的方式奮斗不止的競技場。比如,你必須得面對這個時刻:必須承認萵苣被種得太深,或是沒有澆夠水,不要希望明天它自己就會長出來的,要再挖出來才行。你會為沒有鄙視體力勞動而感覺良好。這就是園藝的全部意義---性格培養。這就是為什么亞當就是一名園丁。
但是,可以想象的是,我們的祖先都曾是織工、鞋匠或其他什么的,但是,會是園丁嗎?當然不會,只有園丁可以不斷地喚回這么多希望,無論干旱、臺風或是自己的愚蠢,今年他會做得好!把這種上帝給它唯一的創造物挑選的自欺欺人的工作留給上帝自己吧!
為誠實起見,我想應該補充的一點是,上面的文字是在12月最冷的一天寫的。